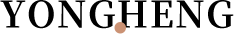江村调查记(上)
-
江村是太湖边一个村落的“学名”。这个村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36年来这里调查,写成《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言》)。开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闻名于世。
费孝通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26次访问开弦弓村,提出许多农村和农民问题。他在《江村经济》中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1957年重访江村,费孝通感到“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1981年之后,费孝通多次重访开弦弓村,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工相辅”、解决农民建房等建议。
费孝通先生把开弦弓村当做社会调查的基地,强调这是一个观察中国农村的小窗口。笔者在2016年初冬时节,也带着《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来到了这个小村。今天的开弦弓村,合并了周围三个村庄,人口比过去多一倍,成为一个有着5个自然村落的农村社区。吃饭、增收、办厂、建房等都已不再是问题。笔者有幸在费孝通先生上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时的老房东家里住了一夜。
增加农民收入,多少年来都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对老百姓来说,只有收入增加了,各种政策措施才算“落地”。开弦弓村年人均收入已超过3万元,算得上小康了。但笔者在访问中发现,收入多了,农民的“自我评价”却并不高,似乎“获得感”还不强。为何?一些村民和笔者算了几笔账。
村边一位谈姓家庭的主妇详细计算了他们家的收入。这是一个六口之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儿子、儿媳妇和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管家的是这位主妇两口子。儿子、儿媳在纺织厂上班,俩人每月收入7000多元,一年接近10万元;丈夫打零工,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一年3万多元;老母亲每月养老金350元。这两位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养老金加起来是600元,全家养老金收入全年有一万多元。这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在13万元到14万元之间。
费孝通先生当年是以四口人的普普通通的家庭来研究农民正常生活最低开支的:一位老年妇女、一位成年男子、一位成年妇女和一个小孩。现在,开弦弓村农民的家庭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代人一同生活的“大家庭”是普遍现象。谈家四代六口人,基本代表了村里普通人家的家庭结构。这个家庭人均收入2万多元,在村里属于中等水平。一方面,主人承认村里有不少人比他们富裕;另一方面,她说,他们家的生活也能反映人们“怎样过日子”。
算完收入账,这位主妇又算了支出账,得出的结论是:“所剩无几,并不富裕。”每月买菜、买米等伙食开支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一年2万元左右;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是每年3000元,买商业保险支出5000元,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其他生活类开支,如买衣服、玩具、营养食品等还得有25000元左右;丈夫抽烟,每天开支15元至20元,一年6000多元;儿子和儿媳妇每年穿衣、出游等生活类开支2万到3万元。此外,这个家庭每年还得有15000元到20000元走亲访友的礼仪类支出。亲朋好友盖房子、孩子婚嫁、老人生病等,都得随礼。全家一年总开支在10万元以上。开支与十三四万元左右的收入相抵,每年结余三四万元。这家人住在一栋上下两层的楼房里,是10年前建的。这位主妇说:“年收入十来万(元)的家庭,在村里不能算有钱。”
一年多少收入,农民才能有富裕的“自我认同”?笔者在一位养螃蟹产老乡那里找到了答案。这位老乡叫周文官,65岁。9年前,他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租赁了20亩地,开始养蟹。他家是一个五口之家,周文官夫妇和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孙子。儿子儿媳妇每年打工收入8万元左右,而他养蟹收入平均也在七八万元左右。加上老伴在厂里打零工每年挣三四万元,他大致估摸,全家每年收入二十万元。他的家庭开支大致与谈家相当,需要10万元。这样,周家每年可节余10万元。老周感觉自家“算得上富裕”。他说,去年刚刚新盖了房屋,上下两层别墅,花费100多万元。他们告诉笔者:一个家庭每年节余10万元,10年多就可以盖新房子。“这样生活才过得下去。”
攒钱10年盖房,正好不耽误下一代结婚成家,自己生活也不受影响。10年,一个孩子正好从少年长成青年。这是一个农家两代人“更新”的时间。看来,农民收入不仅是一个经济数据,更包含着农家接续更替的社会意义。只有收入节余能够完全满足农家接续的需要,农民才有“获得感”。
把工厂建到乡下,以工厂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解决农民有粮而钱不够花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之为“农工相辅”。但是,乡村留得住农民,才能实现“农工相辅”,尤其要留住青壮年劳力才行。在啥状况下,农民才能安心农业“不离土”?开弦弓村的蟹农给了笔者一些启示。
笔者在小清河边遇到刚刚从市场送蟹回来的周文官,正巧,周根全也来他家闲坐。我们三人一起算了算养蟹与打工的收入账。两位老周同庚,都是65岁,而且9年前同时租田养蟹,每人都租了20亩。在同一块土地上,每亩地的租金也都是1000元。
他们对养蟹的开支高度一致,都说每年得11万元左右。蟹苗需要2万元,租金2万元,饲料4万元,还要买一种下在地里的花苗,开支2万元,农药花销8000元左右,电费和其他开销2000多元。这样算下来,20亩螃蟹成本支出,不算劳动力工资,是11万元左右。
养蟹收入不是一个固定数字。周文官告诉笔者,他们养了九年螃蟹,除了有一年因灾绝收之外,收入最好的年头在10万元以上,少的时候也有五六万元。9年下来,每年平均收入七八万元。现在的价格,大蟹在市场上每斤卖100元,中等个头的40元,小个的16元左右。
“养蟹抵得上打工收入。”这是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笔者在江村调查了10多位农民,一般打工者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收入最高的是纺织车间的挡车工,每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但能做挡车工的多是年轻人,像老周这样上年岁的人,在工厂打工收入每月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所以,他们都觉得“养蟹和打工差不多”。
不同的是,养蟹更自由。周文官介绍了他们的“作息时间”:一般早上三四点到地里收蟹,八点之前送到市场。上午忙家务,下午到地里照看一下,时间长短不一。而且一年之内,也不是天天如此。春节过后,有两三个月不用下田,到五月份开始忙,秋冬卖蟹季节才忙些。
按照两位老周的养蟹收入估算,20亩地年纯收入七八万元,亩均收入4000元上下。这一个数字背后,有两个条件一定要考虑:一个是开弦弓村现在有9个纺织厂,距离村子不远处的庙港镇,还有多家纺织厂。这里的工厂吸纳了村里大多数农民就业。笔者了解到,开弦弓村民人均3万元纯收入中,工业收入占86%,农业收入只有6%。再一个条件是,全村2965亩耕地集中到74家专业户开展水产养殖。农民在工厂充分就业,才有农田规模化养殖。农田规模化经营,是保证务农与打工收入相当的条件。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收入”达到了打工收入,他们就会安心农业生产,村庄才能实现“农工相辅”。
开弦弓村的农田耕作经过了几轮变化。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写道:“一个旅客,如果乘火车路经这个地区时,将接连不断地看到一片片的稻田。据统计,开弦弓村90%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桑树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发展蚕丝业。”(《江村经济》第二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兔毛值钱,村里人又大量养兔,费孝通先生的《三访江村》记录了家家养兔的盛况。2000年之后,随着水产养殖效益的显现,开弦弓村的稻田和桑园面积逐年减少。目前,村里已经没有一分地种植水稻,养蚕的人家也很少了。
农田变迁背后是农作物效益的变化,什么值钱种什么。笔者在走访中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快捷和精准,这也是农民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反应。掌握技术的农民是改变土地耕作的积极力量。周文官曾经是村里的养蚕技术员,后来专门养蟹。有技术的农民更愿意留在土地上经营。同时,开弦弓村农田作物仅仅跟随品种的经济效益在变,运用在农田上的科技含量还很少。当前,村里土地大都用来养蟹,笔者调查了三个蟹农,其养殖技术是最普通的,除农药使用和设施更新,基本上没有多少技术应用。
费孝通先生向往的“农工相辅”在这个乡村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没有“空心之虞”,没多少老人和孩子“留守”,有的是四世同堂的家庭。这种和谐景象让笔者这样一个熟悉北方农村的人十分羡慕。但是,要巩固“农工相辅”,除了农田的规模化经营,恐怕将来还得在土地上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含量,技术优势才是农业比较优势的可靠“保证”。
理解今天的开弦弓村,工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这个2000多口人的村庄,有9个工厂。距离村庄4里路的庙港镇,有更多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存在。这些工厂吸纳了开弦弓村人最多的就业。村会计介绍,村里40岁到50岁的劳动力,不论男女,几乎都在纺织厂打工。
乡村工厂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收入,也在改变着农村社会保障结构。笔者在村部会计那里了解到一个数字: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有399人,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社保,其余参加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人,大都参加了城镇社保,他们往往是在工厂参加社会保险的。
笔者走访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两家工厂。晓春针织厂是一个作坊式工厂,设在一栋三层的小楼里。这个厂一般有10个工人照看数台针织机,最多时15人,其中有5人是开弦弓村的。田园纺织厂规模大一些,庞大的生产车间里,数十台纺纱机哒哒作响。厂里会计告诉笔者,工厂是由开弦弓村人开办的,70多位工人中有20多人是开弦弓村人,其余工人都来自附近的村里。纺织厂女工居多,不少外地女工直接嫁到了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的工厂发展了几十年,依然透出“乡土特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农民“兼业”。工厂忙的时候,多增加工人,而生产淡季就减少工人。打工农民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织布车间有70多岁的老人在忙碌着。田园公司一位47岁的倪姓女工告诉笔者,她从17岁就开始在纺织厂上班,原来是挡车工,一直干到41岁。家里房子盖起来了,孩子也长大了,自己身体不如以前,于是到这里来做织布工。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劳动量减轻很多。
田园纺织厂传达室的大爷姓吴,已经74岁了。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7点回家,月工资2000元。他和老伴还有养老金收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孙子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老人说:“我们不缺钞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闲着,所以到女婿的工厂来坐坐,看大门。天热了,还要去种种菜,搞点农业。”
“兼业”也许是帮助农民充分就业最现实的选择。在乡村附近成长起来的工厂,劳动力来源大都是农业效益提高后“溢出”的农民。他们年龄大小不一,文化高低不同,如果追求一种“标准化格式”,必然会把一些人“挤出”工厂。而乡下工厂用工的弹性,适应了农民的兼业需要,也是“乡土化”的最好体现。
如果以纺织机械作为参照物,来考察开弦弓村的纺织企业,每个工厂都换了好几代机器。和所有的工厂一样,升级换代是这些工厂发展的内在要求。有趣的是,技术升级并没有完全改变工厂管理的乡土化。笔者按照以往惯例,找村干部帮忙联系两个工厂去采访。他们建议笔者自己去找。没想到的是,竟毫不费力就进入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没有受到任何“盘问”,笔者就到了生产车间,在机器旁大声和那些有空闲的工人说话。后来又登上二楼,找到了厂里的会计。他熟练地操作着电脑,查找一些笔者问到的数据。植根乡村的那种人与人的信任,在这些现代机器轰鸣的工厂里仍然保留着。田园纺织厂有一个现代化的推拉式大门,传达室吴大爷通过两个按钮,遥控大门的开闭。进入大门,这里还养着两条狗。老人说:“它们是用来看门护院的。”
今天的开弦弓村有多家工厂,加上周边工厂用工数量多,农民就业很充分。村会计告诉笔者,村里30岁到60岁之间的劳动力,不论男女,都有打工收入。但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进纺织厂的已经不多,大部分人从事别的行业。村里人给出的回答是:从事纺织业很辛苦,年轻人更喜欢文案策划等比较轻松的工作。
上一辈人和下一代人职业内容的变化,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村庄环境的基础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年轻人一定不会和上辈人走同样的路。如果说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送进纺织车间,是过去30多年的历史进步,那么,开弦弓的年轻人从纺纱机旁走向更加多样的职业岗位,是又一个有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没有纺织行业的发展那么轰轰烈烈,但它的未来一定比已发生的变化更值得期待。
江村是太湖边一个村落的“学名”。这个村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36年来这里调查,写成《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言》)。开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闻名于世。
费孝通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26次访问开弦弓村,提出许多农村和农民问题。他在《江村经济》中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1957年重访江村,费孝通感到“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1981年之后,费孝通多次重访开弦弓村,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工相辅”、解决农民建房等建议。
费孝通先生把开弦弓村当做社会调查的基地,强调这是一个观察中国农村的小窗口。笔者在2016年初冬时节,也带着《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来到了这个小村。今天的开弦弓村,合并了周围三个村庄,人口比过去多一倍,成为一个有着5个自然村落的农村社区。吃饭、增收、办厂、建房等都已不再是问题。笔者有幸在费孝通先生上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时的老房东家里住了一夜。
增加农民收入,多少年来都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对老百姓来说,只有收入增加了,各种政策措施才算“落地”。开弦弓村年人均收入已超过3万元,算得上小康了。但笔者在访问中发现,收入多了,农民的“自我评价”却并不高,似乎“获得感”还不强。为何?一些村民和笔者算了几笔账。
村边一位谈姓家庭的主妇详细计算了他们家的收入。这是一个六口之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儿子、儿媳妇和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管家的是这位主妇两口子。儿子、儿媳在纺织厂上班,俩人每月收入7000多元,一年接近10万元;丈夫打零工,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一年3万多元;老母亲每月养老金350元。这两位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养老金加起来是600元,全家养老金收入全年有一万多元。这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在13万元到14万元之间。
费孝通先生当年是以四口人的普普通通的家庭来研究农民正常生活最低开支的:一位老年妇女、一位成年男子、一位成年妇女和一个小孩。现在,开弦弓村农民的家庭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代人一同生活的“大家庭”是普遍现象。谈家四代六口人,基本代表了村里普通人家的家庭结构。这个家庭人均收入2万多元,在村里属于中等水平。一方面,主人承认村里有不少人比他们富裕;另一方面,她说,他们家的生活也能反映人们“怎样过日子”。
算完收入账,这位主妇又算了支出账,得出的结论是:“所剩无几,并不富裕。”每月买菜、买米等伙食开支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一年2万元左右;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是每年3000元,买商业保险支出5000元,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其他生活类开支,如买衣服、玩具、营养食品等还得有25000元左右;丈夫抽烟,每天开支15元至20元,一年6000多元;儿子和儿媳妇每年穿衣、出游等生活类开支2万到3万元。此外,这个家庭每年还得有15000元到20000元走亲访友的礼仪类支出。亲朋好友盖房子、孩子婚嫁、老人生病等,都得随礼。全家一年总开支在10万元以上。开支与十三四万元左右的收入相抵,每年结余三四万元。这家人住在一栋上下两层的楼房里,是10年前建的。这位主妇说:“年收入十来万(元)的家庭,在村里不能算有钱。”
一年多少收入,农民才能有富裕的“自我认同”?笔者在一位养螃蟹产老乡那里找到了答案。这位老乡叫周文官,65岁。9年前,他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租赁了20亩地,开始养蟹。他家是一个五口之家,周文官夫妇和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孙子。儿子儿媳妇每年打工收入8万元左右,而他养蟹收入平均也在七八万元左右。加上老伴在厂里打零工每年挣三四万元,他大致估摸,全家每年收入二十万元。他的家庭开支大致与谈家相当,需要10万元。这样,周家每年可节余10万元。老周感觉自家“算得上富裕”。他说,去年刚刚新盖了房屋,上下两层别墅,花费100多万元。他们告诉笔者:一个家庭每年节余10万元,10年多就可以盖新房子。“这样生活才过得下去。”
攒钱10年盖房,正好不耽误下一代结婚成家,自己生活也不受影响。10年,一个孩子正好从少年长成青年。这是一个农家两代人“更新”的时间。看来,农民收入不仅是一个经济数据,更包含着农家接续更替的社会意义。只有收入节余能够完全满足农家接续的需要,农民才有“获得感”。
把工厂建到乡下,以工厂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解决农民有粮而钱不够花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之为“农工相辅”。但是,乡村留得住农民,才能实现“农工相辅”,尤其要留住青壮年劳力才行。在啥状况下,农民才能安心农业“不离土”?开弦弓村的蟹农给了笔者一些启示。
笔者在小清河边遇到刚刚从市场送蟹回来的周文官,正巧,周根全也来他家闲坐。我们三人一起算了算养蟹与打工的收入账。两位老周同庚,都是65岁,而且9年前同时租田养蟹,每人都租了20亩。在同一块土地上,每亩地的租金也都是1000元。
他们对养蟹的开支高度一致,都说每年得11万元左右。蟹苗需要2万元,租金2万元,饲料4万元,还要买一种下在地里的花苗,开支2万元,农药花销8000元左右,电费和其他开销2000多元。这样算下来,20亩螃蟹成本支出,不算劳动力工资,是11万元左右。
养蟹收入不是一个固定数字。周文官告诉笔者,他们养了九年螃蟹,除了有一年因灾绝收之外,收入最好的年头在10万元以上,少的时候也有五六万元。9年下来,每年平均收入七八万元。现在的价格,大蟹在市场上每斤卖100元,中等个头的40元,小个的16元左右。
“养蟹抵得上打工收入。”这是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笔者在江村调查了10多位农民,一般打工者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收入最高的是纺织车间的挡车工,每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但能做挡车工的多是年轻人,像老周这样上年岁的人,在工厂打工收入每月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所以,他们都觉得“养蟹和打工差不多”。
不同的是,养蟹更自由。周文官介绍了他们的“作息时间”:一般早上三四点到地里收蟹,八点之前送到市场。上午忙家务,下午到地里照看一下,时间长短不一。而且一年之内,也不是天天如此。春节过后,有两三个月不用下田,到五月份开始忙,秋冬卖蟹季节才忙些。
按照两位老周的养蟹收入估算,20亩地年纯收入七八万元,亩均收入4000元上下。这一个数字背后,有两个条件一定要考虑:一个是开弦弓村现在有9个纺织厂,距离村子不远处的庙港镇,还有多家纺织厂。这里的工厂吸纳了村里大多数农民就业。笔者了解到,开弦弓村民人均3万元纯收入中,工业收入占86%,农业收入只有6%。再一个条件是,全村2965亩耕地集中到74家专业户开展水产养殖。农民在工厂充分就业,才有农田规模化养殖。农田规模化经营,是保证务农与打工收入相当的条件。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收入”达到了打工收入,他们就会安心农业生产,村庄才能实现“农工相辅”。
开弦弓村的农田耕作经过了几轮变化。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写道:“一个旅客,如果乘火车路经这个地区时,将接连不断地看到一片片的稻田。据统计,开弦弓村90%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桑树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发展蚕丝业。”(《江村经济》第二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兔毛值钱,村里人又大量养兔,费孝通先生的《三访江村》记录了家家养兔的盛况。2000年之后,随着水产养殖效益的显现,开弦弓村的稻田和桑园面积逐年减少。目前,村里已经没有一分地种植水稻,养蚕的人家也很少了。
农田变迁背后是农作物效益的变化,什么值钱种什么。笔者在走访中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快捷和精准,这也是农民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反应。掌握技术的农民是改变土地耕作的积极力量。周文官曾经是村里的养蚕技术员,后来专门养蟹。有技术的农民更愿意留在土地上经营。同时,开弦弓村农田作物仅仅跟随品种的经济效益在变,运用在农田上的科技含量还很少。当前,村里土地大都用来养蟹,笔者调查了三个蟹农,其养殖技术是最普通的,除农药使用和设施更新,基本上没有多少技术应用。
费孝通先生向往的“农工相辅”在这个乡村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没有“空心之虞”,没多少老人和孩子“留守”,有的是四世同堂的家庭。这种和谐景象让笔者这样一个熟悉北方农村的人十分羡慕。但是,要巩固“农工相辅”,除了农田的规模化经营,恐怕将来还得在土地上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含量,技术优势才是农业比较优势的可靠“保证”。
理解今天的开弦弓村,工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这个2000多口人的村庄,有9个工厂。距离村庄4里路的庙港镇,有更多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存在。这些工厂吸纳了开弦弓村人最多的就业。村会计介绍,村里40岁到50岁的劳动力,不论男女,几乎都在纺织厂打工。
乡村工厂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收入,也在改变着农村社会保障结构。笔者在村部会计那里了解到一个数字: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有399人,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社保,其余参加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人,大都参加了城镇社保,他们往往是在工厂参加社会保险的。
笔者走访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两家工厂。晓春针织厂是一个作坊式工厂,设在一栋三层的小楼里。这个厂一般有10个工人照看数台针织机,最多时15人,其中有5人是开弦弓村的。田园纺织厂规模大一些,庞大的生产车间里,数十台纺纱机哒哒作响。厂里会计告诉笔者,工厂是由开弦弓村人开办的,70多位工人中有20多人是开弦弓村人,其余工人都来自附近的村里。纺织厂女工居多,不少外地女工直接嫁到了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的工厂发展了几十年,依然透出“乡土特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农民“兼业”。工厂忙的时候,多增加工人,而生产淡季就减少工人。打工农民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织布车间有70多岁的老人在忙碌着。田园公司一位47岁的倪姓女工告诉笔者,她从17岁就开始在纺织厂上班,原来是挡车工,一直干到41岁。家里房子盖起来了,孩子也长大了,自己身体不如以前,于是到这里来做织布工。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劳动量减轻很多。
田园纺织厂传达室的大爷姓吴,已经74岁了。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7点回家,月工资2000元。他和老伴还有养老金收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孙子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老人说:“我们不缺钞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闲着,所以到女婿的工厂来坐坐,看大门。天热了,还要去种种菜,搞点农业。”
“兼业”也许是帮助农民充分就业最现实的选择。在乡村附近成长起来的工厂,劳动力来源大都是农业效益提高后“溢出”的农民。他们年龄大小不一,文化高低不同,如果追求一种“标准化格式”,必然会把一些人“挤出”工厂。而乡下工厂用工的弹性,适应了农民的兼业需要,也是“乡土化”的最好体现。
如果以纺织机械作为参照物,来考察开弦弓村的纺织企业,每个工厂都换了好几代机器。和所有的工厂一样,升级换代是这些工厂发展的内在要求。有趣的是,技术升级并没有完全改变工厂管理的乡土化。笔者按照以往惯例,找村干部帮忙联系两个工厂去采访。他们建议笔者自己去找。没想到的是,竟毫不费力就进入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没有受到任何“盘问”,笔者就到了生产车间,在机器旁大声和那些有空闲的工人说话。后来又登上二楼,找到了厂里的会计。他熟练地操作着电脑,查找一些笔者问到的数据。植根乡村的那种人与人的信任,在这些现代机器轰鸣的工厂里仍然保留着。田园纺织厂有一个现代化的推拉式大门,传达室吴大爷通过两个按钮,遥控大门的开闭。进入大门,这里还养着两条狗。老人说:“它们是用来看门护院的。”
今天的开弦弓村有多家工厂,加上周边工厂用工数量多,农民就业很充分。村会计告诉笔者,村里30岁到60岁之间的劳动力,不论男女,都有打工收入。但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进纺织厂的已经不多,大部分人从事别的行业。村里人给出的回答是:从事纺织业很辛苦,年轻人更喜欢文案策划等比较轻松的工作。
上一辈人和下一代人职业内容的变化,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村庄环境的基础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年轻人一定不会和上辈人走同样的路。如果说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送进纺织车间,是过去30多年的历史进步,那么,开弦弓的年轻人从纺纱机旁走向更加多样的职业岗位,是又一个有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没有纺织行业的发展那么轰轰烈烈,但它的未来一定比已发生的变化更值得期待。